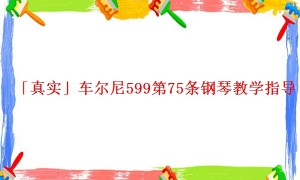在长假期间,我再一次进入巴赫。他的三百余首众赞歌无疑是初学和声的绝好材料,巴赫在此把他的和声引入了规范的传统和声体系,我在80年代外文书店购得此书,当时公家也敢盗版(还有肖斯塔科维齐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平均律则把他一切和声与复调对位理论上的可能性付诸实践,那些和声至今仍让所有的最前卫的摇滚乐手痴迷不已。平均律我用烂过五套,每套都密密麻麻地作了记号分析:一套标和声调性,一套标自己的钢琴指法。我可以常年不见外人,足不出户,只要有键盘、吉他、巴赫的平均律。我使用MIDI键盘,外加好的MIDI音源,调成harpsichord的音色(其实用什么音色这类感官的东西不是很重要)。
不管是对平均律分析和声还是研究编排指法,都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这里面大部分作品都有三个优点好处:
1是旋律不够优美、2是没有多少感情,更没有多少“高潮”,3是不炫耀指技。
一旦作品旋律很优美、充满了感情、或手指快速如飞,那就完了。因为这样以来,你一旦练好了这样的作品,就立即会有一种冲动,那就是表演给人看、给人听—-这就如同伸出了讨饭的手(一个朋友总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当然这样骂人不好)。而巴赫的平均律不会这样。它无须使人交际:即使下围棋也要交际,因为你要找一个对手。能和巴赫的这类音乐相媲美的,就是纯数学、数论。这种音乐和数学一样逻辑严密(只要把一首赋格用键盘“推导”两边,就可以记住,可以“复盘”),和数论一样,不仅是科学,也是优美无比的艺术(抽象的优美,想想伽罗华的群论)。这种东西自然会使你长时间不出门也不感到孤独。
巴赫本人也一定和陈景润一样,除了迷在他的头脑里以外,其他方面一定是个“傻子”“呆子”。陈景润走路撞到一棵树上,连忙说“对不起”。巴赫的朋友们帮巴赫料理他老婆的后世,问他一些事,他边弹琴边说“问我老婆去吧”—这是我小时听作曲家邵广深说的故事。如果他不傻不呆,哪有时间专心致志研究。当入侵军队的士兵冲入阿基米德的房间,他正在地上证明一道数学题,死到临头,还说,让我算完再说,不要挡住我的光线。
当有学生问欧几里德,你教的东西有什么用时,欧几里德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给这位学生说,你可以走了。
人们想在巴赫无数的数学证明般严谨而有趣的赋格中找出一个漏洞,结果都是失败。这种音乐和纯数学一样,可以是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但创造她的逻辑却是客观严谨的。创造出的产物可以无比的严谨、优美并可以同时兼具高度的独创性和洞察力。
初学吉他的学生,会对吉他上的许多“特殊奏法”很感兴趣“,如小鼓奏法、泛音奏法,等等,其实这些表面上花里胡哨的东西一会儿就可以学会,然后兴趣很快就会降温。接着又会对轮指、音色变化等等东西感兴趣。而这些东西并不高深,学会了意思也不大。
小孩子会对1个苹果、2个梨感兴趣,大了以后会知道抽象的数字也满有意思。能领会无具体所指的抽象数字是人类的一次智力飞跃。进一步的抽象,是用字母表示数,(如问题:一绳测井深,单股长出a尺,双折短出b尺,问井有多深,绳有多长?)。更进一步的抽象,是群论和抽象代数,甚至用字母表示运算、表示方程、表示一个命题。
真正专业的作曲大师必会对抽象结构感兴趣。只有天才才能意识到他对面坐的是一个天才,而天才一个世纪也没几个。所以天才是由隔代天才来欣赏的。一个智商只有80的人会认为对面智商200的人的智商才有20,还会动不动教训他一顿。
伽罗华不到30岁就在和政敌的决斗中被刺死。他的群论论文给柯西也看不懂,还被当垃圾揉成一团扔进纸篓。他考学时他认为主考官问了他一个愚蠢的问题,竟然气得一拳打在考官的脸上。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这就是真正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