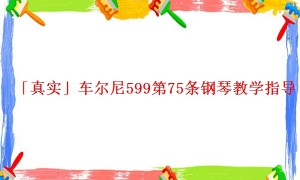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孩子们成群的中小学里,老师对学生的业余文艺活动非常关心,经常挂在嘴边问学生的几句话便是:“你钢琴弹到哪本练习曲了?业余钢琴考级考过几级了?你手里都保存着哪些比赛获奖证书?”回答不会出现困难,但也不会那么轻松,因为在无形的回答后面隐约可见的是:已把孩子们的弹奏分出了高低,这在孩子回答的神态上来看,他们早已掂量过回答的分量。但不管你对这种分高低的方法提出何种辩诉,在习惯的眼光下,人们一贯就是按这种以“质”分高低的章程办事的。
“量”往往体现在钢琴学习者在一定时间内所弹奏或浏览曲子的数量。这对业余学习者来说,就是包含他所接触的全部曲目—其中有练习曲和各类乐曲;这对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每学期老师为他们在教案中制定的学习量,这个学习量必须完成,因为这是考查一个学生学习进度,决定一个学生升留级的重要依据之一;这对一个钢琴家来说,“量”意味着他能展示给听众曲目量的多少。曲目库的大小折射出钢琴家的演奏才华高低,更透析出一个钢琴家应对复杂的演出市场的能力。
我们知道: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钢琴学习中“质”和“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在我们钢琴学习的群体中重“质”轻“量”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这与钢琴学习中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潮相关联,因为“质”能立竿见影带来眼前利益,而“量”非但不能,还要付出,消耗眼下的精力,自然重“质”轻“量”,这条所谓的捷径对很多人是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例如比赛得奖、考级通过……会立即产生荣誉感和名人效应,其中成绩突出者能脱颖而出成为众目睽睽的明星。同时指导教师也能在获胜的大蛋糕上分得一块,在以后的教师职称评定中也为自己的功绩浓浓地写下一笔。至于学生的基础建设、长远规划等问题当然就会忽视。
这样导致业余钢琴老师的钢琴谱架上仅放着一本考级书。我们钢琴专业老师也只把培养独奏演员、比赛选手为己任,给学生拔几首大曲子南征北战去参赛的做法,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赞许。它也造成我们一些在国内、国际比赛获奖的选手,由于后续发力乏劲而成为钢琴舞台上昙花一现的过路客。
当今世界上名目繁多的钢琴比赛比比皆是,只要你留神数点,几乎每天都有赛事。如何走出比赛利益的诱惑,摆正“质”与“量”的关系,这也是世界钢琴界共同面临深层思考的问题。
面对这潮水般袭来的比赛,很多人感到兴奋,有强烈参赛的欲望,因这提供了一次舞台实践和选手间相互切磋的机会;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对众多比赛是感到沾沾自喜,认为多多益善,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比赛路上,一心期盼奇迹出现,自己能被评委所垂青。
事实上,世界乐坛已淡化各种比赛的效应。例如在美国钢琴杂志上一篇评论“比赛太多了”的文章中,作者追溯了不少比赛获奖选手的后续发展情况,发现他们后来干哪一行的都有。
一些著名的钢琴家,权威教授也对比赛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著名朱利亚音乐学院卡普林斯基教授说:“现在比赛大小无数,总有成功的机会,赢得比赛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天才,那只是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作为一生成败的论断。”又如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桑多尔认为:“钢琴比赛已非常不健康,已是一种传染病,全世界都感染上了。从前也许只有5到10个重大比赛作为演奏家事业的起步,现在太多,对青年艺术家的害处极大。我常常担任国际大赛的评委,像是在扮演上帝。”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也提出了一个可能伤害青年艺术家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比赛。他说:“因为比赛青年人获胜了,出了名,那当然观众对他的期望更高了,压力就更大了。这不利于青年人的舞台生涯和成长。”霍洛维兹又说:“他愿意一场场的在舞台上赢得自己的声望,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样做已让他受益无穷。”我国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在一些全国性钢琴研讨会议上直率说:“不同意全国性比赛搞得多,不同意经常参加比赛的尖子学生围着比赛曲目转而放弃日常进行的教学计划。”
当今国外的钢琴教学除了强调学生自己的思考能力外,已更注重大量曲目的掌握上。当一个成功的钢琴家,他的一切音乐活动必需要以丰厚的音乐会曲目为依托,不然就会出现后劲不足,难以立足在表演舞台上。在此值得一说的是:现在的演出公司、唱片公司的经纪人对钢琴家要求越来越苛刻,他们根据市场需求,要你录音、演出。记得罗马尼亚著名钢琴家鲁普和我国著名小提琴家薛伟在采访中都承认对这种要求的演奏生活不适应,最终前者采取了回音乐学院深造,后者决定去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任教。
在《钢琴艺术》2006年第一期中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朱贤杰在接受采访时介绍道:“当代钢琴大师罗文塔尔的保留曲目有六十部协奏曲,盖扎·安达有三百部作品,霍华德录过一千多首作品,有一百多部作品随时可以演奏,巴伦博依姆18岁之前就演了全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朱贤杰最后还就中国钢琴家的成长问题发表了自己发人深省的看法,他说:“今天中国的钢琴界不是在呼唤大师吗?那就先看看当代国际大师手上的曲目吧!”
大家知道现已蜚声海内外的我国青年钢琴家郎朗。他的突破发生在1999年,在最后的一分钟他接到邀请,替代患病的美国著名钢琴家安德烈·瓦茨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合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上演出,结果用当时评论界的反应来说可用“狂喜”二字来形容,郎朗取得了成功。有人称他为意外的成功,其实这意外的成功也不意外,因为此时的郎朗手中已掌握了三四十部钢琴协奏曲,如果没有这个家底,那他即使遇到更好的机会也能骤然失之交臂。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初,俄国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离开俄国开始在欧美演出生涯的一幕。他在汉堡一连举行三场音乐会并不叫座,因为当时欧美听众还不太了解他。一天下午霍洛维兹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回到了旅馆门口,他看到当地经纪人正迫不及待地找他,原因是预定当晚演出的钢琴家因生病不能演出协奏曲了,经纪人请求霍洛维兹替代登场。霍洛维兹意识到这是生命转折中的一次大好机会,他只要求得到一杯牛奶就冲入房间穿演出服、刮胡子,然后登台和乐队合作演出了。当演奏结束时,全场听众起立,歇斯底里地叫着,指挥更是不停地拥抱霍洛维兹,整个音乐厅几乎被激动的听众所掀翻,从此欧美各大城市纷纷热情地拥抱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年轻钢琴家。
郎朗和霍洛维兹出神入化的境遇何其相似!他们的人生都被幸运之神敲开了大门,他们神奇的故事令人羡慕不已,但在这故事的背后谁能知道他们为这一天所付出的泪水和辛劳?所以说,他们才是命运的真正主人!
在钢琴的乐坛上,历史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令人费解:这就是一些钢琴家在重大比赛获奖后,或在演出声誉获得市场火暴回馈之时,也就在自己前途将达到如日中天的片刻,却突然宣告隐居,然后再在舞台上迅速消失,在若干年后突然又复出并取得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这难道是这些钢琴家在跟平日欣赏与关爱他们的听众玩捉迷藏游戏?这难道又是这些钢琴家们在舞台上作秀搞噱头,制造爆炸新闻?非也!这种现象出现自有它的隐情所在,让我们举例加以剖析:
1960年意大利钢琴家波利尼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他是89名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表现征服了听众,全体评委一致评他为第一名。当时的评委长鲁宾斯坦感叹地说:“真不知道,我们评委中是否有人能弹得比他好。”这次比赛使波利尼名声大振,瞬间闻名全球。但此时波利尼却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离一个钢琴家还差得很远,在曲目量,尤其在近现代作曲家的作品掌握上深感缺憾!于是他很快决定在乐坛上销声匿迹,这一去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他拜师求教,潜心钻研技艺。通过这八年的埋头学习,波利尼不但提高了技艺,更主要的是还大大扩大了曲目量,为他今后在艺术上的辉煌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俄国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曾多次从舞台上隐居,最长的一次是1953年至1965年,整整延续了十二年不在听众面前露面。在这十二年里,霍洛维兹潜心研究了克列门蒂、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等作曲家的作品。
著名的美国钢琴教育家罗森说得好“今天钢琴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尽快掌握三百年来所积累的浩如烟海的钢琴文献。”为此目的,钢琴界的上上下下对钢琴学习中的“量”和“质”的关系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他们日渐在理论上明确了钢琴学习中“量”的聚集,到一定饱和点便能促使“质”变,缺失“量”变的“质”是单薄的,难以成气候,甚至会随之萎缩的。仔细观察我们的钢琴队伍,我们一定会发现在我们周围有不少茁壮的有前途的小苗,我们要让他们吮吸着量变积攒起来的营养将来生成钢琴艺术的参天大树。
在苏联的钢琴教学中,创立了一种叫粗线条教学法,此种教学法不是涵盖整个教学,而只是整个教学的一部分。它的教学内容和特点正如著名音乐家列夫·巴伦鲍伊姆曾给这种粗线条学习法下的定义:“当他们分析了谱子上所写的一切,并能正确的、有内涵的按乐谱要求演奏乐谱之后,对作品的练习才告一段落。”瑞士19世纪后半叶女钢琴家奥古斯塔·布瓦西耶在如何理解粗线条教学上也曾用描写她与年轻的李斯特见面时的情景加以解读,她说:“李斯特不赞成一字一句地去背诵作品,他认为只要能够掌握作品的总体风格即可……”这样钢琴学习者可通过粗线条学习法尽可多地了解作曲家及他们的作品。学生们能够充分“理解”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音乐现象来丰富自己的音乐感觉,以利于自己朝未来钢琴家的方向成长。
粗线条教学内容在我们日常钢琴教学中,其实就是一种老师布置的浏览曲目,它不要求在舞台上展示,是仅供学生了解、熟悉钢琴作品之用,是钢琴教学上的一种辅助手段。一个有经验的钢琴老师都会围绕着教案,布置若干浏览曲目让学生们吃小灶。我还记得20世纪著名的钢琴家埃米尔·吉列尔斯,青少年时代他的老师赖因巴尔德教授让他接触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赖因巴尔德教授有两条教学原则是:“第一,青少年学生钢琴知识的全面发展,视野的扩大重于他们把个别作品演奏得非常成功,甚至闪闪发光;第二,如果学生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显示出来演奏的天赋,则应该让他们扩大曲目量,掌握他们音乐记忆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