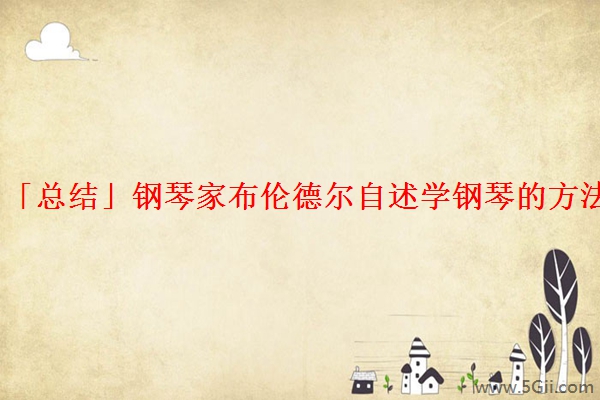
为了使自己在钢琴上继续取得进展,我常听阿瑟·鲁宾斯坦(ArthurRubinstein)和威廉·肯普夫(WilhelmKempff)的演奏。我很有兴趣听我的年轻同行们的演奏,但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回过头去听费肖尔、科托以及斯纳贝尔的录音。实际上。我对指挥家和歌唱家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他们那里有许多可学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我喜欢听贝多芬(德国钢琴家 – 贝多芬简介)和李斯特弹奏。我认为李斯特一定比今天所有的钢琴家更优秀。他一定能在音乐上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你只要看看他年轻时写的那些东西,例如那些最难的练习曲如十二首超技练习曲(etudesd’executiontranscendante)。你不能想象今天有任何人能在技巧上比他更好。也许有些人能够较少地弹错音符,但那又怎样呢?并不能表明他们就更伟大。
我愿意亲自见见舒曼、贝多芬、莫扎特。莫扎特或许是最有趣的人,因为很难想象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认为有谁弄清了这一点。我希望继续走向成熟,我还只是40出头,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尽管总地说来我对评论家的评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一次在纽约,一位评论家暗示说:我所弹奏的贝多芬将在未来几年中走向成熟。我希望这位评论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一直在从贝多芬的作品中发现新的微妙之处。新的发现必须一直继续下去。如果我认为我已穷尽了整个贝多芬,我想这将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他的作品是那样惊人的复杂,新的洞察和发现简直没有尽头。我不需要批评家来告诉我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保持自己个人的判断力。他不应该太多地受批评家的影响。有时候批评家说的话可能是正确的,但这通常是在音乐会的演出效果方面。如果我得到的印象是我弹奏得不好,那往往是场地在传达音响效果方面的原因。例如,我在台上听见的声音可能极大地不同于人们在观众席上听见的声音,而这将改变整个演出的形象,正像你在不同的功放器和喇叭箱上放一张同样的唱片,其效果可能发生极大的改变一样。有时候同一张唱片可能产生出不同的、令人失望的效果。在整个传输渠道的某一个地方,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会失落。因此在演奏过程中我不得不不断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演奏在听众席上产生的效果怎样?他们听见了些什么?” 因此当你问到我的成功,以及任何艺术家取得的成功所具有的性质,我能够回答的只是指出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并承认成功的性质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显然,我没有早期的成功可谈论。当我25岁的时候,我不属于那种在体格上就能广泛赢得公众的人。我的确属于局外人,而我也希望做一个局外人。我用某种嘲讽、鄙视的眼光去看待公众,在那些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自己。我试图自己独自做成一切事情,这使我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事业。但这一过程也有某些好处,它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我的音乐修养,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人、了解人。我能够轻松悠闲地研究音乐演奏会的种种事实井观察这架机器如何运转,我对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将不得不怎样树立自己的形象也有了更好的观察和透视。我有幸没有处在必须设法维持早期取得的成功的巨大压力下,那种压力甚至可以使最大的才能遭到毁灭。我并不认为有什么成功秘诀,如果真有什么秘诀,我知道我并没有遵循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