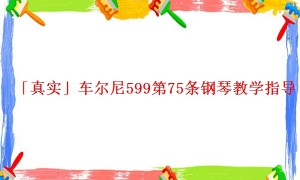钢琴是全功能的,旋律、和声、对位,它包了。异常复杂的多声部,它也可以做出来。有位钢琴家说得好:它不是一件乐器,它是几十件。它那88键的广大音域差不多就等于乐队中从低音提琴到短笛的全部音域。一架小小的钢琴俨然是一支大乐队。钢琴家“指挥”这支“乐队”,比一个乐队指挥更要来得挥洒自如,得心应手。
同人声相比,金属弦上叩击出的音响,照理说是比“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更不如了,但钢琴音乐中许多“如歌”的名篇,如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五首》的慢乐章,如贝多芬《悲怆》中的《柔板》,如肖邦《降E大调小夜曲》,这许多熨人肺腑的音乐,听着只当是在听一个歌手的吟唱,全忘却了那是从一副钢铁之物中传出来的。
而且,钢琴音乐也不以“如歌”为极致,为尽其能事,须知音乐中不是只有“如歌”,也还有“如话如语”、“如踊如舞”。即以“如歌”而论,也还有各种情绪之歌,这种种,钢琴都可以表达。
还可以申论的是,钢琴也并非为了要同歌喉或别的乐器争一日之长短而创造的,它不以仿其他人之声为高,而是为了补他人之不足。凡深谙其本性的大师,如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德彪西等,他们为它谱出的最能发挥其特色的音乐,也才是真正钢琴化了的钢琴音乐,那种效果是其他各种乐器所不可替代的。连集管弦乐器之大成的交响乐队也不可能。此其所以将管弦乐曲“译”为钢琴曲,同原作比,当然有所失;反过来将钢琴化的作品“译”成乐队曲,往往所失更大。像莫扎特、贝多芬与肖邦的许多作品是不宜改为乐队曲的。名指挥魏因迦特勒好心“译述”贝多芬的Op.106,不但无功,反遭诟病。肖邦之作,竟是不可“译”,一译便俗,例如《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
这样一种无法替代的原版、原味,当然说明了它的独特价值,但同样了不起的是,它又是一架艺术翻译机。
从各种别的乐器的独奏曲、独唱曲、合唱曲(连同伴奏部分一并代劳),到规模宏大的交响音乐,统统不难“译”为“钢琴版”。这种多译功能对19世纪以来交响音乐之普及,发挥了莫大的作用。无印刷术,莎剧难以普及;无钢琴,歌剧与交响音乐也难以为广大爱乐者所尽情享用。主要就在于它的这种演奏改编曲的功能。
19世纪的人还没有唱片、录音机好利用,如果不是钢琴,许多人将成为对名作无知的人。
乐器之王的诞生,自然是18、19世纪音乐文化大潮的时势造英雄,它是顺天应人应运而生的;然而英雄又造时势,对音乐大潮有推波助澜之功。厥功甚伟!
它一来到人间,便通过制作者与作曲家、演奏者、巧匠与巨匠们之间的互促,以日新月异之势不断完善,终乃成为作曲家、演奏家们的喉舌。
肖伯纳盛赞印刷术普及莎剧有功,仿此,可以说,缺了钢琴这位要角,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之轰轰烈烈的局面也难以想象吧!
学习音乐的人离不开它。它不仅是学和声、作曲的助手,又是分析作品的释读工具。作曲者与键盘已不可须臾离开(除了绝无仅有的例子,柏辽兹)。莫扎特在巴黎,肖邦在马约卡,身边无琴,害得他们难以作曲。其他各种乐器如小提琴等,常常需要它的合作,因为这些乐器只能奏光秃秃的旋律。众多的爱好者离开它也就无从在自己家里咀嚼音乐粮食了。
它又像药里的甘草,同人声、同什么乐器都和得来,或为之伴奏,或与之相和。在一架琴上,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几人联弹。
作为专业用,它的技艺、表现能力是无止境的;当普及性的乐器,它既可个人自娱,又可大家同乐。正因其如此有用,可喜,于是从教室到音乐会,从歌剧舞剧排练场到沙龙,它无所不在,普受欢迎。泰坦尼克邮轮上,兴登堡号飞艇上也少不了它,甚至沙场上也有它的声音回响。呜呼,可谓盛矣!
“众器之中,琴德为优”,是中国古人嵇康赞七弦琴的话。借此语赠钢琴,也当之无愧。
钢琴300年,前100年是它成长、奋斗,与古钢琴共处、竞争的百年。中间百年是它优胜、夺魁的盛世。近百年虽有人厌其泛滥成灾,怨声四起,且又逢新的劲敌当前——广播、电子琴等等,然而乐器之王的声威犹在,并不见有下世的光景。尤其在中华,钢琴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千上万的琴童,放弃了童年的欢乐,埋头在键盘上苦修苦练。有多少琴童在学琴,也就有多少父母在陪学陪练,同作钢琴梦。
遗憾的是,琴童的父母们自己并不是钢琴爱好者。也绝少见到有青年识得钢琴的真价值,迷上它,用它来开拓自己听乐的境界。这又是钢琴的不幸了!
有感于此,从年轻时便时常梦见我当时可望不可及的洋琴的笔者,不惮自己的浅陋,也甘冒为钢琴商当推销员之嫌,愿为钢琴鼓吹,期望爱乐而尚未深知琴趣的朋友们,爱上它,迷上它,享受它。如此,也便实现了笔者的本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