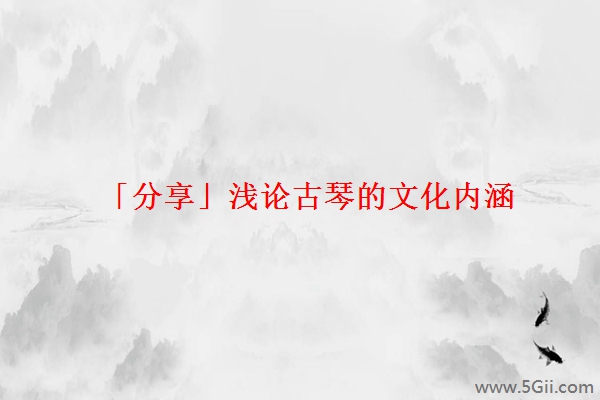
文/董蓓蓓
浅论古琴的文化内涵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王维的咏琴绝句《竹里馆》,表达了古人对古琴艺术的一往深情。就在不久前的2003年,中国的古琴被联合国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当中,这不可不说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中国的古琴原是仕族们借以“明志”的工具,故有“士,无故不彻琴”的说法。在周代,琴是十分“私人化”的东西,它不会用在宴乐之中。原因之一是琴的发音很轻弱,不足以从朋客们的咀嚼声中送入耳膜,它只是宜于向自己表达理想和情绪的乐器。周代以前,琴是民间的,从不象古代君王夜宴时的钟、鼓那样因“声音洪亮”而为贵族所重视。当时,它的号召力是比较差的。可是到了周代,它成了仕族门的“家乐”。仕族可以在私人的访谈交流时从琴音中探听出彼此的“心声”!所以,琴也许就这样“重要”起来了。上古, 琴是没有琴谱的,有一种人是职业的“琴师”,他们一辈子往来于仕族子弟之间,教琴、演琴。那时还出现了世代教琴的琴师家族,如孔子的老师叫师襄,即琴师世家“师”的后代(师的古意就是教琴者的意思)。在师襄之前,还有因为在教琴时得罪郑卫侯的宠姬被鞭打了三百鞭的师曹,有在晋侯面前反对“靡靡之乐”的师旷。可以说孔子是受过耳传口授的专业训练的,故而,操琴成了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必学的“六艺”之一,它是文人提高自身修养的必备的武器。中国的文人抚琴,目的不仅仅是单纯将音乐呈现出来而已,其中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听一个人弹琴,如同在读一个人的心,琴彷佛像一面镜子,将人内心世界映照出来,借着琴音的传达、抚琴的姿态与神韵,能了解这个人的性情。五千年来,中国的“古琴”除了演奏外,还承继着儒、道两家的修身养性、教化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形成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内涵。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传统琴曲主要用五声音阶,即五正音,这可说是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音乐上的落实,而琴乐清虚淡静的风格和意境则主要为道家思想的反映。整个古琴艺术被称为琴道确实有其道理,因为对古琴的欣赏和认识不能只单一地从其音乐曲调去理解,而是从多方面去理解琴而为道的涵义。
一、古琴与教化
蔡邕的《琴操》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宋史乐志》:“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汉代扬雄在《琴清英》中也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可见伏羲氏 、神农氏作琴,如同周公制礼作乐、孔圣人以“德”教化人民一样,都是以乐教化人心的。
中国的琴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乐教、诗教传统有关,儒家文化儒始终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念,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文化占有优势地位,他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在琴学中就成了“琴以载道”的思想,文人的琴也就与乐教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先王乐教”,周代也有周公制乐的记载,这种礼乐教化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娱乐,更是在中国长期的政治、伦理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于是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其实,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乐教并没有失传。中央音乐学院古琴大师李祥霆教授就曾经举办“唐人诗意即兴演奏音乐会”,这种普及性音乐会上观众当场命题,大师即兴演奏,一唱一和,别开生面。李祥霆教授将唐诗与古琴演奏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众多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欣赏到诗、乐智慧的至臻至美境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民族器乐“乐教”传统的独特体现。在儒家看来,琴乐不仅可以使人从个体上达到身心的和谐、畅快,还能通过与礼的融合,使个体的情感在自然满足的同时,受到礼的规范和制约,自然性情感与社会性情绪和谐起来,使纯感性的情感打上理性的烙印,消除对立,达到“人乐和一”的完美境界。在道家看来,琴乐可以使人由蝇营狗苟的世俗之人上升为“神人”、“圣人”,从而弃绝个人的利害达到“物我两忘”的“无我”化境。同样,道家庄子进一步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而那些杂乱、浮躁的声音都不是美声、不合常理,化境之中自在松弛弹奏的“和而不乱”才是美乐。
明代琴师徐上瀛在他的《溪山琴况》中写到,“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首重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循徽叶声,辨之在指,审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凡弦上之取音惟贵中和,而中和之妙用,全于温润呈之。若手指任其浮躁,则繁响必杂,上下往来音节不成其美矣。故欲使弦上无煞声,其在指下求润乎?”圣人造琴以理天下人之性情,而琴乐在乎中和圆润才能入耳,任由手指无章法地乱弹杂乱的声音就是噪音。其实,无论东西方乐器在奏乐之前都要调音以正视听也是这个道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这里的“音和”上升到“家和”、到“人和”,最后到儒家的“天人和一”和道家的“乐与天通”就是要达到“乐教”的最终目的。“中和”而不走极端,与自然相谐,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思想之一。
总之,以“和”为理想的古琴艺术,它体现了以“声和”为特质的“和”性音乐美学观,它同时承载起善与美、人与神、历史与未来的神圣使命,表达了“德音不瑕”的庄严命题。
二、古琴与修养
古琴作为一种艺术,始终代表着中国文人修身养性、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古人抚琴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与琴曲的情绪,融合其中,进一步影响内在心理的调整,久而久之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据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不进。师襄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黯然而黑,几然而长,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师襄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
这段话的大致意义是:师襄子四次劝说孔子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四次拒绝,第一次时孔子说:“我刚学会这首琴曲的曲调,还没有理解它的结构。”第二次时他说:“我已经理解这首琴曲的结构,但还没有领会它的意蕴。”第三次时他说:“我已经领会了这首琴曲的意蕴,但还没有了解作者的为人。”第四次时他说:“我已经了解作者的为人,但还没有把握作者的形貌。”第五次师襄要孔子学新曲,他说:“通过乐曲,我仿佛远远望见作者心胸宽广、思想深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乐曲。他皮肤黝黑,身材颀长,称王天下,接见诸侯,想来恐怕是文王吧!”师襄子离坐起立,拜了两拜,说:“说得好!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乐曲是文王作的。”所以,孔子凭借文王所作的乐曲,了解了文王的胸襟。正是在孔圣人这样的先贤榜样的感召下,历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以“抚琴”作为人生修炼的功课,并从中领略“曲”-“数”-“意”-“人”-“类”的逐步升华的学养意义。可见,古琴不但有乐教的功能,同时还能够激活生命的情感空间,前承古人、后继来者,与古人今人产生巨大的心灵的共鸣,以达到陶冶性情的目的。
自号“六一居士”的北宋文人欧阳修是有名的琴家,他曾在《六一居士传》中这样写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语虽诙谐,但也是他这类文人寄情于琴的生活写照。更为有趣的是,欧阳修还从琴中发现了治病的新功能,他在《送杨置序》中写道:“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体也。”他认为弹琴、听琴可以达到养生,乃至治病的目的应该说是有科学依据的,例如《平沙落雁》等曲情绪平和,就很有益于一些患者治疗的。
可见,弹琴的过程是美妙的。但是,弹琴也是必要有其环境的,在空灵的环境中的弹琴,自然而然的,人的性情也可以得到修养和升华。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有过这样一段话:“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上头,或在林石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崖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
弹琴要求琴者要把心安定下来,浮躁者是弹不出美音的,全神贯注地将自己内心的心弦与古琴的琴弦相融合,用自己的气息、熟练的手法,传达出琴的意趣和自己的意念,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体会出心灵与琴弦契合的妙趣,体会出超凡脱俗的意境,如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何病而不可除?
中国的古琴,是中国最有风骨的乐器,古人讲“琴棋书画”, 把琴放在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代表着一种气, 一种度, 更甚至代表一种高扬的人格。在某个寂静的夜晚,听一曲宋琴大师刘赤城演奏的《流水》,或放一首明琴大师张子谦的《平沙落雁》,那感觉,真是酣畅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