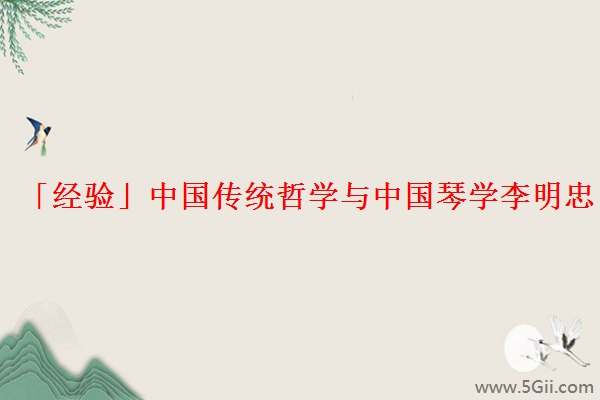
无论古琴在古代得到怎样的美化,怎样的点染;近现代遇到如何的冷落,使人们感到陌生。但它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中为数不多的,贯通着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一种悠久的器乐艺术。它毕竟有着自己特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在数千年的春秋岁月中,对华夏音乐文化的开发、积累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数千年闭关自守的国度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生活在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现代文明的今天,随着世界文化的疾速交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进一步融汇,作为一件有着十分系统的琴学体系的古琴,其丰厚的遗产、典型的特点及特殊的艺术功能,将进—步为人们所认识、推广和应用。
由于乐历的久远,数千年来伴随着华夏文化的繁衍、滋生,并一度受到过朝野上下的推重,使得中国琴学中容纳着我们这个民族有史以来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所各有的,以及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哲理心态,汇集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律学、谱式学、音乐史学、哲学、美学……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那种多层次、多色调,博大精微的渊深内涵。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律、调、谱、器等方面都有着丰厚的遗产和显著的建树。
同样,也因为琴史的久远,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为文人、士大夫乃至封建帝王所玩味品赏,孤芳自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偏离现实社会中剧烈复杂的斗争,多侧重于用来表现个体的内在境界,故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出世的消极色彩。
通过探索学习、悉心潜思,本文仅就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以及儒道互补等多方面的联系,浅作论述,以就教于识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情况所致,即,它不象西方美学那样早巳从哲学中派生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是紧密的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交织,浑然融汇(或者说不少美学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目前状况来看,中国传统美学尚未独立,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学科建设。既便是目前见到的一些中国传统美学著作,也主要多在中国传统哲学、理学的范畴内去谈中国传统美学,并没有过多的揭示出中国传统美学形成的明晰的逻辑,更无疏理出其完整的体系。故而,本文凡言所涉及的中国传统美学云云,亦即中国传统哲学种种。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状况、和种种社会原因,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中兰艾混杂,精华与糟粕往往密切缠绕,再由于文献浩繁,积累庞博,欲全面、系统、清晰地条理出二者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力所不逮。因此,本文暂且先论列某些专题。
(一)
根据诸多琴论文献及历代琴人的观念看,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古琴艺术是一种人文与自然高度融合的、抽象的时态艺术。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是什么?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二者有一定的从属,一定的界限,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前者主要是通过阐发抽象的艺术形式给人的各种境界的艺术感受,以及其它间接的社会功能。后者则主要是表述人的精神境界和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思考。
在中国传统哲学这极为广阔的领域中,不论被认为是讲究入世哲学的儒家,或被认为是讲究出世哲学的道家等诸家诸派的思想大家,数千年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真、善、美的议论,其核心,都集中的围绕在对“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这些根本要务的论证、说明、研讨、实践之中。从早期的先秦来看,《易经》所说:“大人者与大地合其德”。《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庄子;齐物论》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了汉代,这种“天人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董仲舒在《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也”。到了宋代这种“天人关系”,又得到了深入的丰富。朱湘在其《语类;卷九十四》中说:“……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自禀受,又各自全俱太一尔”。还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站生,得知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又在于天”。到了明代,这种“天人关系”的概念就更加具体,王守仁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为一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电,日月星晨,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他们之中,无论是以唯物论为基础去解释“天人关系”也好,或是以唯心论的观点去说明“天人关系”也罢,虽然立论的出发点有别,但各白所追求的终旨却不无相同,即天人是相通的。
在这里,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作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
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已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的唯心主义的成份,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
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而呈现于世,而是浓厚的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上述先哲所论“天人关系”招呼应,在琴学论著中如:《太古遗音》所说:“昔者,伏汤氏之亡天下也,仰以观法于天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所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
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
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弹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熟能尽雅琴之所蕴乎?”
苏景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天地之元音,养中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
陈敏子在其《琴律发微》中:“琴由后世得与知者,肇于歌《南风》千古之远,稍诵其诗:即有虞氏之心,一天地化育之心可见矣……,且声在天地间,霄汉之赖,生岩谷之响,雷霆之迅烈,涛浪之陷撞,万窍之阴号,三春之和应,与夫物之飞潜动植,人之喜怒哀乐,凡所以发而为声者、洪纤高下,变化无穷,琴皆有之。”
稽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等等等等。
上述诸种论述中不管有多少传奇的成份,神秘的色彩,但透过这种现象可以窥见:他们均共同的在捕捉或强调那种天、人之间的关系,参天地阴阳、自然万物与琴、人融合为一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哲理观念。
琴论之中这种将天、地、人、器融合为一,以天地人文自然为一体的美学思想,贯穿于中国琴学始终。这种在最根本、最广大的意义上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其意义和表现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这种追求意识到了上乘的琴乐应该是既根源于自然,且符合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艺术。有了这种观念,琴乐的立意便能够逐步达到合规律,合目的的至佳效果,立足这种观念去解决美与艺术,社会内容与艺术形式等重要关系时,无形中避免了由于使人与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相脱节而导致的各种弊端,这种追求既是一种思想境界,思维境界,也是一种艺术境界,同时亦即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那种属于哲学境界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境界归纳为四种;一、自然境界,二、功利境界,三、道德境界,四、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中前两种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不需要怎样的觉解;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用这种境界来衡量,琴史传奇中有这样一个典故:
成连教伯牙学琴三年后,对伯牙说;“我只能传授你弹琴的技巧,若要把琴真正弹好,须再请我的老师方子春来教你。”于是把伯牙带到蓬来山上说:“你在此好好练琴,我去请方子春。”伯牙一人留在荒寂的海岛,海哮风涛,风云变幻,使伯牙顿悟,原来成连老师在教我“移情”。(蔡邕《琴操》)此虽仅属传奇,但却使人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这种将琴乐艺术与天地自然变幻浑然一体的“情景合一”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在指导着琴人的琴学实践,不能不说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琴学几乎从最初的萌生阶段,就深刻的意识到了“天人关系”的统一性,意识到了上乘的艺术应该是融人文、天地宇宙万物高度和谐为“一”的一种综合交融的艺术。按成连教伯牙“移情”的意识去履行,弹琴若能把心体与风雨露电、日月山川等天地自然融为一体,那么这种演奏就能达到王国维对艺术作品所强调的: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的“情景合一”的至高境地。在中国琴学大量的传奇故事中象师旷弹琴可使云鹤起舞,射巴弹琴会令沈鱼出听,伯牙弹琴,其巍巍高山,洋洋流水的立意能被钟子期心领神会等等,都具体地说明了中国琴学艺术的美学思想是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思维观念而形成的。可以说这种思维观念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心态的典型体现。正是在这样一种艺术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琴的演奏,在很早以前的古代就已经达到了深刻的哲理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传世的琴曲《水仙操》、《秋鸿》、《流水》、《渔樵问答》、《平沙落雁》以及大量的琴学论著即是体现这种美学类型的有力的实证。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可以这样说,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特点,由于“情景合一”和“知行合一”是从“天人合一”派生出来的,所以概括起来看这种种“合一”全部都集中在“天”和“人”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归纳起来实质上也就是个“合二为一”的问题。所谓“合二为一”即:合天、人二者为一,合天、人,情景为一,合知、行二者为一,这里的“合二”是指对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而综合合成的“一”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涵量无比博大,经化合融汇而成的“常数”。正如宋代朱长文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结合后文对“知行合一”等所述内涵,用“合二为一”的思维哲理去理解中国琴学的内涵,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露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正象宋代朱熹在其《语类,卷九十四》所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这种“月印万川的哲学观点,恰恰是观察、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琴学所可以借鉴的思维方法。
当然,也无可否认,“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观察事物,分析事物,有其本身的优势,但与“合二而一”相对照,两者总有一位是处于对事物顺向观察,顺向理解的正面。而另一位则处于对事物逆向观察,逆向理解的对面。用上述朱熹所说的“月印万川”为例,如以月为基准去观察,那么万川禀受均来自一“月”,这样看,应该是“合二而一”,若以万川为基准去观察,那么将成为“万川分月”则应该是“一分为二”。因此无论是以“合二而一”的观点去概观琴乐的综合性,或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剖析琴乐的多层面,都不应忽略,人是天地自然阴阳循环的产物,而琴乐是人精神世界抽象思维的发出。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露电、阴晴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决然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的不断变化波动。从这种意义去讲,上品的琴乐表现,应该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合二而一”的哲学规律。
(二)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隋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里现出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
结合明代徐青山在其《溪山琴况》中对和、静、轻、远……24况音声美学和操弄意念的论述来看,如其“和况”所述“有得之弦外者,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粼,而洋洋倘恍,暑可变也,虚堂凝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这种统山、水、寒、暑、天地自然的博大变化,…揽于琴乐演奏意境的追求之中的意念,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情景合一”这一传统哲学思想在琴学操弄境界中的明显体现,其中借寒暑变幻来升华演奏者的演奏意态,并自如地驾驭那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哲理。这就更把操弄琴乐的人(主体)及与之意合的山、水、寒、暑(客体),用意深微地融合为“一”。毋需置疑,“和”况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美的准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境之说,相宜合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恬”况所说:“诸声淡,则无味,琴声淡则有味,味者何?恬是已。味从气出,故恬也。夫恬不易生,淡不易至,唯操至妙来则可淡,淡至妙来则生活,……故于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不味而味,则为水中之乳泉,不渊而洲,则为蕊中之兰苣。”
“淡”、“恬”二者以“妙”暗合,所谓“至妙”是一种精深致微的,无以言状的演奏意态,是一种气度安然莫测的神妙,靠这种神妙来净滤操弄者中和的气度,使琴乐的演奏达到那种声律有节,气韵有度,高洁沁心的艺术境界。
结合“逸”况分析,如其所说:“人必具超逸之品,故发超逸之音。……雍容平淡,养其琴度……则形神并洁,逸气渐来,临缓则将舒缓而多韵、处急则犹运急而不乖”。与其它诸况联系,所谓人必具超逸之品,故发超凡之音的含意应该是:演奏的人,要使琴乐产生出那种高洁逸远的超凡之音,净化之乐,就务必先具备那种超逸高洁的品格。淡泊宁静的气度,还得深知指、弦、音、意的音理,具性情中和,调气静神的功夫,以及与山相映发,与水相涵濡的意态。
这种对人的品格气度,形神韵质与琴乐操弄造诣高度结合的审美追求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情景合一”的美学特点,在琴乐艺术中的典型体现。
另外,在“和”、“静”、“清”、“远”、“淡”诸况中还屡屡可见的贯穿着道家学派对音乐艺术极富深刻哲理的哲学、美学思想。如其“远’况所说:“迟以气用,远以神行。……,至于神游气化,而意之所之,玄之又玄,时为半寂也,若游蛾嵋之雪;时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倏缓倏速,莫不有远之微致,益音至于远,境入希夷,非知音未易知,而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
这里将道家学派所强调的“大音希声”、 (《老子》)“游心于物之初”、“出入六合,游乎九洲”,(庄子《至乐》。《在射》)这种种极富幽深境界和丰富想象力的审美状态有机地融汇到了古琴这种抽象时态艺术的操弄境界之中,不难看出,中国琴学艺术所追求的美绝非单纯听觉直官所感受到的那种音量大,“技巧复杂”,等等外在的音声美,也更不是那种易逝的,不耐人寻味的、浅显的美,而是一种含蓄幽深,纯真质朴的自然的美,是一种超凡纯净,有着深远意境的美。儒道两家的追求在这种艺术境界的深遂处,均有着不同的体现。这种境界既是一种哲学境界,也是一种艺术境界。正象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对“境界”解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为之有境界否则谓无境界。”
根据“情景合一”这—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来看,琴乐中“情”之所指应是在操弄琴乐时,人的精神的主观创造,“景”之所指应是宇宙的万景万物和总体,“情景合一”是指在操弄琴乐时人的精神创造与宇宙间诸景诸物的感应及融合。
当然,不同操弄者的不同境界和精神创造有着不同的感应效果,有那种对各种景物的直官感应所产生的“情景合一”的境界,如前文所举伯牙在孤岛上的“移情”效果,也有那种通过精神的创造,或者说是意态的转换而产生出与景物极端对立而又高度统一的“情景合一”的效果。如《溪山琴况》在“和”况中所说的那种“暑可变也,虚堂凝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的转换意态。
细致的体味,中国传统艺术中象司空图的甘四诗品,冷仙的琴声十六法,徐青山的廿四琴况及大量的书论,画论都突出的在强调着“情景合一”的种种意境。琴乐作为一种极其抽象的时态艺术,其音声、音量只是一种表面的物理存在,只有将音声、音量按音乐表现的需要去提炼、升华,使其达到某种境界时,它才能启发、唤起人内心的思维、联想、想象等诸多感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感情与之共鸣,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对各种自然意境和思维意境的一种追求和神往。这种种追求的境界能否实际达到,对操弄琴乐的人来说,似乎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则是操弄的人在心境上能否“涤除玄览”(老子)去追寻那种“心包万里,心包万景”(朱熹)的境界。如叶嘉萤在《加陵论词丛稿》中对王国维“境界”的解释所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世界未经吾人之感受之功能予以再现时,并不得称之为境界……”
纵览大量琴书,几乎所有琴曲都有其特定的立意和境界,或是抽象的具体,或是具体的抽象。凡真正的琴家,无不对曲意去做深刻的体味、勾画,凡真正的鼓琴、操弄者,无不是在对某种境界去感受,去履行,去再现。
(三)
就古琴艺术而言,如果说“天人合一”、“情景合一”是一个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艺术境界的话,那么“知行合一”则似乎更侧重于体用关系。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领域中,知行问题,一般的被看来是个认识论和应用学二者的关系问题。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它要求人们对诸事诸物不仅应知(认识)而且应行(实践,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一哲学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如孔子所说的“君子耻其言过其行”指的就是一个知行一致的问题。荀子强调“行”为知的目的。但同时也承认“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所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知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圣人也。”朱熹说:“知行常相须”。还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也说:“知之真切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微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是后世学者分为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还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在古琴浩繁的琴学论著和悠久的实践传统中,历来有着将创作、操弄、斫琴、琴论综合兼备于琴家一身的风习,这种经年累月誉成的风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这一哲学要务在中国琴学中所得到的具体体现,东汉琴家蔡邕可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从创作、操弄兼备于琴家一身的相互作用看:
如果把琴曲的创作阶段作为一种对琴乐的认识过程,把操弄作为一种对琴乐的实践过程的话,那么,创作这—阶段的心理动机,制曲技法的施展,必然经创作者本人去进行操弄实践的体味检验。而经过操弄这一实践阶段的体味检验之后,所取回的种种直接感受,心得体会,再反馈给创作者本人;以便继续将这种种经过实践所得到的心得体会复注于自己的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再创作,然后再经由创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去作再一次的实践的操弄、体味。如此这般不断循环,直至作品和操弄达到一种相对的成熟。这样,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地去完成一个从认识(创作)到实践(操弄),再从实践到认识集于一身的一个“体用合一”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多数琴曲又继续通过历代琴人世世代代的反复实践,不断完善,可以说现在存见的传世琴曲中大部分曲日都集结着不同时代的诸多琴人的智慧。
可以说这种体用过程是包括琴乐在内的一切器乐艺术步入高深境界的最佳途径。就连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也大抵如此。
不好想象,没有一定古琴弹奏水平或对古琴艺术没有一定了解的作曲家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乐曲:同样,没有一定二胡拉奏水平或对二胡艺术没有一定了解的作曲家,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二胡曲。在这种实实在在的学术现象面前,一切未经“体用”(即认识、实践的反复过程)检验的作曲技巧在实际的使用面前总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而把对器乐规律长期认识、实践的体用积累(经验)施展于器乐的创作中却往往又显得是那么的自如、于练,有时甚至是信手拈来。中国琴学中,这种知行密切相伴的体用风习则是由始以来为历代琴家所履行的一种典型特点翻阅数以千记的大量琴曲,几乎见不到一首琴曲不是经操弄的琴家所亲自创作方得以留传;也几乎见不到一首琴曲是经由不会操弄者的创作而得以传世,可以这样说,琴曲的创作者必定是琴曲的操弄者。
在中国悠久的琴学传统中,那些将创作、操弄、斫琴、琴论兼集于琴家一身的风习,更值得人们去悉心体味,这种风习对数千年的琴学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试想,郭楚望若无深厚指弦功夫,娴熟的制曲技能,那么其立意深远,结构严谨,跌宕起伏的传世之作《潇湘水云》将何以产生?
试想苏膺若没有相当的操弄阅历和对古琴音声的长期品味,那么,不论他怎样去精心地剖修唐琴槽腹,也决无法体察出纳音聚韵的奥秘,沈括若不进行多次的斫制或监制实践,谅他无论以怎样的天才,也绝难以体察、领悟出那种轻、松、脆、滑的岁古良材在斫琴中的妙用。从这种意义去推理,历代琴家中不少文人、学士乃至王侯们的斫琴嗜好绝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功利行为,也绝非是一种以出于单纯兴趣的偏爱,而是动机十分明确的在履行着“知行相须”的体用过程。
试想,若没有对操弄、创作、琴论兼备一身,互为作用的综合体味,蔡邕也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琴曲创作,琴学著述以及“焦尾琴”的有趣传说。没有历代琴家在操弄、创作、斫琴、琴论,这诸项相关密切的领域内去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一长期的体用过程,琴学中那些奇、古、润、透、静、匀、圆、清、芳,四善,四虚等对音声品质精到的审美总结,以及浩瀚的琴论、典籍,均将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历代琴家在操弄、创作、斫琴、琴论这诸项相关密切的领域内去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一长期的体用过程,那种长期为经验所证明,决定音声类型的“唐圆宋扁”和琴书中大量斫琴制度的记载亦均将成为无本之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操弄、创作、斫琴、琴论,这种兼备于琴家一身,并互为作用的风习,使历代琴家有意无意地在履行着一种“知行常相须”的体用功能。这种“知行常相须”的履行,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这一哲学要务在中国琴学中的典型体现。
(四)
通过前文中对“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简略论述,透过皮相,探视其形骸深处。对其思想背景、文化背景进行仔细分析的话,可以看出支撑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两家各循其旨,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学说主要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理规范,政治观念之中,而不长于抽象玄思的一种“实践理性”,而道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人与外界的、超功利的、自然无为的超脱意态,这种意态的美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
儒家以其“尽善尽美”的“实践理性”学说格守,而道家以其“尽真尽美”的追求而超脱,儒道两家,尽管呈现着诸方面的对立,但是,在中国琴学这一十分抽象的艺术领域中,对立的两家,确实存在着互补互益的现象。若再深入的作一比较,则还可推见,儒家的入世思想之长,(就其面对社会现实,强调琴乐对道德、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及追求“尽善尽美”等思想而言),恰恰是道家的出世思想之短;而道家的出世思想之长 (就其超越功利,主张“无法之法”,追求“尽真尽美”的境界而论)恰恰又是儒家入世思想之短。这种无可否认的状况恰恰形成了两者互补互益的客观前提。
如儒家那种“乐与政通”等思想,它虽然有其面对现实社会的一方面,但是那些把君、臣、民、事、物等与琴乐本身毫无关系的政治说教、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非常牵强地附会于琴乐艺术之中,有些观念甚于到了扼杀艺术发展,使本来纯真的琴乐艺术遭到了人为扭曲的地步(如六要、六忌、七不传,“将军门里无琴声”,唯琴为器不入歌舞场……)这就直接的使琴乐艺术承受了很多本身特质以外的负着物,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琴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面对儒家在艺术领域这种极大的片面性和弱点,道家以其独特的姿态出现:如《溪山琴况》,“远”况所说:“调古声淡,渐入渊源……此稀声之引伸也,”“静”况所说:“淡泊宁静,心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矣。所谓希者,至静至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与羲皇之上也。”类似这种超脱自若,不受任何人工雕琢的“尽真尽美”的追求,对儒家在艺术领域中的薄弱和不足给予了有力的补充。
道家的种种主张和追求,在中国的琴学等传统艺术领域(如诗、书、画……)之中,经常冲击着那种僵死的政治法度以及人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对艺术创作的桎梏;为艺术创作步入高深的境界,常常起到儒家所无法达到的积极作用。如:道家对音乐寥寥四字“大音希声”的追求,就远远超过了儒家那种:乐可以兴一帮之主,可以亡一国之君。声音之道与政通也。等等牵强附会的,对艺术社会功能的不适度的夸张。
有人从艺术规律的审美角度去评判儒道两家的作用,认为:儒家美学是同政治伦理学结在一起的美学,大半是政治伦理学,小半是美学,只有道家美学才是纯粹美学。这种说法似不无道理。
结合《琴况》等大量琴学论著,如“和”、“静”、“清”、“远”诸况所述,“不味而味,则为水中之乳泉,不馥而馥,则为蕊中之兰苣……”,“ 邪而存正,拙俗而还雅,舍媚而还淳”,“不求不兢,如雪如冰,如松之风而竹之雨,间之滴而波之涛”;“大音希声”,以及《琴操》所说:“昔伏羲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等。从这种种琴学论述来看,其中既有着对琴乐品质的标格,同时,又有着对那种“渐入希夷”美好境界的神往,既有着体现儒家刻意人工“修身理性”的意旨,同时又有着体现道家返朴归真“返其天意”的追求。儒道两家在古琴艺术的高深层面互为作用,达到了一种超越各自自身的言外的和谐,这不能不说是儒道两家相济共美,互补互益的理想状态。这种儒道互补互益的理想状态,只有在琴乐这类十分抽象的时态艺术领域内,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由于琴乐具备着抽象这一十分有利的特质,所以使它极便于为儒、道诸家派提供他们之间对立、分歧以外的诸多“言外和谐”(或者说是“言外共性”)所可以共同融汇的理想寓所。正是在这种兼收并容的寓所之中,才使诸家诸派那些“言外和谐”、“言外共性”等诸多因素得以充分的汇集,如此造就形成了古琴音乐这一类中国传统艺术的多色调、多内涵、多层次的特殊色彩。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中国琴学,乃至中国传统艺术品独有的一大特点。
对立的儒道两家对琴乐社会功能的观察角度虽然不同,但双方在琴乐高深艺术殿堂中的相处,却又是那么的和谐,以致使我们无论从《溪山琴况》中任何一况或传世名曲中任何一曲去观察,很难使人明晰地指其中某一况或某一曲是纯粹的儒家入世思想;而其中另某一况或另某一曲是纯粹的道家出世主张,似也不能机械的去说,其中某一况或某—曲是儒的外衣,道的实质;而其中另某一况,或另某一曲是道家的外衣儒家的实质。
有人对诸多琴曲加以归纳,将另一部分琴曲指定为“反映儒家思想的琴曲”,将一部分琴曲指定为“反映道家思想的琴曲”,还将再一部分琴曲指定为“反映清淡玄学精神的琴曲”等等。
对于极为抽象,而又牵涉十分复杂的琴乐艺术,用一种机械的分类方式一一罗列,确指某曲是反映的道家思想,某曲是反映的儒家思想……等等,似欠妥当。
因为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完整性、丰富多样性,其特质的形成,除了特定的地域环境外,思想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其决定的因素,在中国极为丰富的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两大支柱,数千年来始终统治着中国的学林,造就着历代的学问先哲,涵泳出包括自然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门类、各种学科,作为滋生于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之中的琴、乐、画、书、诗、词等等艺术项目,应该说也都是这种传统文化完整性的一种具象缩影的体现。尤其是琴乐这一十分抽象的器乐艺术,由于其抽象的性质、特征非常突出,便无形中适合于各家各派那些“言难尽意”的艺术追求,以及那些对立以外的言外共性,在其中无形的汇集。也就是说,由于琴乐种种特定情况所致,它所禀受的绝非只是一家思想,一派主张;而是吸收融化着有益于琴乐艺术升华的各种营养,各种营养互为作用,促使着琴乐艺术晶多色调、多内涵、多层次的完整形成。
也只有在琴乐这种深具抽象特征的时态艺术领域内,儒道两派以至其它各派的某些思想、追求,互补互利,相益共美地融合,才能体现得那么浑然,那么默契。因此在古琴大量的琴曲中,就任何一首传世的名曲分析,其中不仅有着一定成分的儒家思想风格,同时有着一定成分的道家思想风格。
两种思想风格甚至多种思想风格,在艺术的抽象中相互交织,浑然天成,从这种意义去看,任何一首传世的琴曲,就其体现的风格和包涵的内容去进行分析,它绝不可能是—种纯而又纯的儒家思想的反映,也绝不可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道家思想的体现。正象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所说:“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的,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那么数千年来滋生、繁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特定沃土之中的中国琴学,似乎应该也是既入世的又出世的。
(作者系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