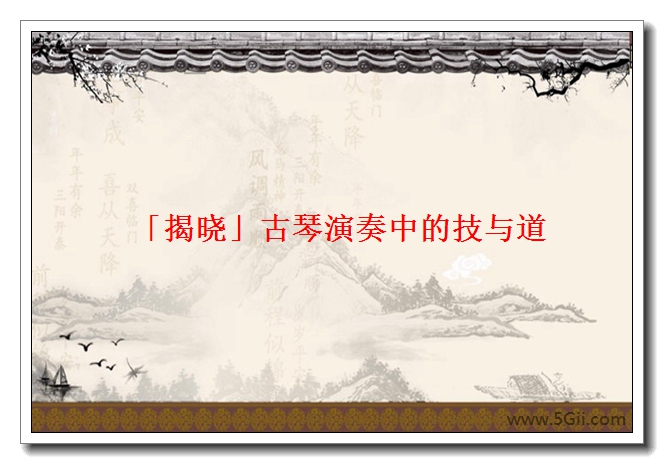
作者:刘承华
技与道的问题是音乐演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技术问题在演奏中是一个极为基础、也无法绕过的问题,但仍然十分明显的是,技术并不能解决音乐中的全部问题,相反,如果处理不当,它还可能带来其它问题。我们经常说某某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其实技术也是。然而,在中国古代古琴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被琴人提出,并作了不同但均是有效的解决。这不同的解决方式主要在文人琴和艺人琴两个琴艺传统那里完成,而其解决的方法,又都与一个哲学的寓言有关,那就是庄子的《庖丁解牛》。
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寓言讲起。
一、《庖丁解牛》中的两种“道”
庄子的《庖丁解牛》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为了便于更细致地了解,我们还是将其主要内容抄录于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马砉)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个故事整个围绕的就是“技”与“道”的问题,也就是“技”、“道”关系问题,即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我们先来看看《庖丁解牛》文本当中陈述了一个什么内涵。
庖丁解牛的技术很高超,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形象化的描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马砉)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段话说明庖丁在宰牛过程中得心应手,已经超越到一种自由的境地,我们常用“炉火纯青”或“进人了化境”来形容技术的高超,这段话便是对“化境”的描述。然后,文惠君对这样的状态大为赞叹,说:“技盖至此乎”,也就是说,技术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啊。在这里提出“技”的问题,并引出庖丁的一番议论,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这是他针对文惠君“技盖至此乎”的回答,同时又提出一个新概念“道”的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不是“技”而是“道”,“道进乎技”,就是“道”比“技”更近一层的含义。紧接着,他对自己宰牛的过程作了描述,说:“始解牛,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见全牛”。三年之后,看到的不是全牛而是牛身上的肌理,就好像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人体解剖图一样,现在经过许多年的实践之后,“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官”,指感官,“神”指一种精神,也就是说:手里的刀本能地、自然而然地顺着牛的肌理把牛一块块卸下来,不是我在指挥,而是一种神的力量在指挥着,表明一切都达到了非常自如的境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是说在牛体内的每个关节、每个块面之间,虽然空隙很小,但再小也是空隙,以薄到极致、几乎没有厚度(“无厚”)的刀进入这个空隙,当然会运行自如。以“无厚”对“有间”,用的是夸张的手法突出两者,一个被放大,一个被缩小。小的东西进入大的空间,自然会“游刃有余”。顺着纹理而运行,就不会有阻碍,刀也就不会有损伤。这种境地,在庖丁看来,就不是“技”的问题,而是更进一层的“道”的问题。文惠君对他的解释很满意,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就是说,本来是问你宰牛的事情,却得到了养生的道理。
这个故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庖丁所讲的一句话:“道也,进乎技”。问题是,这句看来十分明白的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加深思,会认为它很简单。“道者,进乎技”,意思是:我重视的是道而不是技。但是,仔细想想,在上述文本中,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进乎技”的“进”理解为“转向”,也就是说,我关注的并不是“技”,而是另外一种东西“道”,由对“技”的追求引向对“道”的追求。所以“道”比“技”更进一层。应该说,中国古代在对庄子《庖丁解牛》故事的理解中,大部分人取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其中注云:“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这里表达的就是一个“转向”,我所关注的不是“技”,而是寄托在“技”中的“道”。然后,他又以疏的方式进一步解释说:“舍释鸾刀,对答养生之道,故倚技术,尽献于君。”这是从形态层面而言,讲的是宰牛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与宰牛之技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郭庆藩所指之“道”就是养生之道,是技外之道。接着他又解释说:“进,过也,所好者养生之道,过于解牛之技耳”,同样也是说明“进”为“转向”之意,只不过转向后是比转向前更高的一个层级。
第二层含义,将“进”理解为“超越”。“超越”是拥有某种东西,又超过了它。哲学当中有“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包含着它以后又做的否定,也就是超越它,超越意味着达到一个更高水准,更高水准中包含着一个低层次水准,就如我们读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包含了高中、初中、小学一样。在这里“超越”包含了什么内涵?实际上,由于我们已经完全地、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问题,它不再是问题了,我就超越于它,获得了自由。在前面庖丁所讲的话中,最贴切地作了注释。他说:开始时,所见是全牛,三年之后,所见不是全牛,再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官知止而神欲行”,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地步。这些说明:一开始靠技术,当技术问题被自己攻克之后,就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道”的境地,此“道”正是庖丁所关注的,是对“技”的一种超越。这与第一层含义的不同在于:前者“技”与“道”是两件事情,“道”是技外之道,从宰牛转向养生,只不过用另外一种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后者“道”为技中之道,是对技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技和道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阶段,就是说在“技”的掌握过程中,进入一个更高的被称为“道”的阶段。
二、在古琴演奏中的体现
这个故事所包含的这两种理解,如果用文本当中的内容来表示,则一个是文惠君的理解,认为“道”是技外之物;一个是庖丁本人的理解,认为“道”是技中之道,是技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人们运用庄子
这一哲理的过程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两种技道关系。而且,在古琴演奏当中,就涉及了庄子这两种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从庄子文本来解读古琴演奏中的技道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古琴演奏中的“技”与“道”,实际上就是庄子《庖丁解牛》中两种“技”“道”关系的翻版。
古琴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是文人琴,一个是艺人琴。两大传统分分合合,它们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又有着不同的精神特征。现在我们从演奏的技道关系来看《庖丁解牛》文本中两种技道关系在两种琴的传统中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我们看文人琴中的技一道关系。
由于文人琴的基本特点是它的非职业性,他们弹琴主要用于自娱和修身养性,所以比较注重个人弹琴时的感受,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又由于文人拥有比较多的文化资源,有着很多文化创造的冲动,所以,在琴的活动中,他们也常常把这些东西转移进去,构成琴的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弹琴过程中,他们强调琴中的哲学、文化、社会、文学等各种各样的意蕴,在琴学研究中,也很注重对这些方面内涵的挖掘。因此,琴很早就形成为“琴学”,它不仅仅是一种“艺”,而且还是一种“学”。在中国语汇当中,特别在琴学中,“技”和“艺”往往联系在一起,琴作为艺实际上就是把琴主要作为一种技术来看待。但在文人琴当中,文人更注重在琴中得“意”,而不是把琴看成一种艺术或技术。在他们看来,琴中的技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阳修说:“夫琴之为技小矣”。,就是说琴中的“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就等于转移了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技”小,是因为他看到了另外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道”。甚至连身为艺人琴家的徐上瀛,受到文人琴的这一观念的影响,也秉持着文人琴的一些观念,其中即有以“道”论琴的方面。他说:“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斯逾久而逾失其传矣”,就是批评当时人把弹琴仅仅归结为“技”的现象。广陵派代表人物徐祺也提出“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也是反对把琴当成艺术,把琴仅仅视为“技”。明清时的琴人,大都接受了文人琴的重要观念:不主张琴是艺术,更不主张琴是技术。琴技为小,必然有另一个东西为大,那就是“道”。文人琴特别强调“道”的问题,以至于现代许多琴人一提到“琴”就认为是道器、法器。
那么,在文人琴中,“道”指的是什么?实际上,“道”就是指我们的精神修养,指琴的声音之外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我们的精神感悟,包括情感、操守、品格、文化品味。因此,在这里,“道”和“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文人琴讲的“道”是技外之道,而不是技中之道。在他们看来,“技”只是弹琴的技巧,是琴当中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只是感性的一种手段、一种物质载体,但琴真正要表现的是高级的东西,而且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总体上可以说,对古代文人来说,琴是修身养性的,尤其对人的品格有养成作用,对人的道德有提升作用。文人琴接受了庄子《庖丁解牛》中文惠君的观点,把“道”看作技外之道。
再看艺人琴,艺人琴也有其技道关系。艺人琴的基本特点与文人琴正好相对。前面说文人琴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非职业性,重自娱,而艺人琴最基本的特征是他们以琴为职业。过去我们笼统地说古琴是文人音乐,从它整体性质上说,这句话不错,但如果说古琴都是文人琴,都是修身养性的,那就错了。因为在古代琴的发展史当中,在琴人的庞大队伍当中,有相当一批很知名的一流琴家,他们琴技很高超,是职业琴家。他们中有的在宫廷专为皇帝弹琴,有的到大贵族、官僚家中成为门客,有的在社会上收徒教人弹琴,后来有人开了琴社琴馆,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僧人琴家和道士琴家。所以,艺人琴在古琴发展史上不是没有作用,相反,它是起着中坚的作用。尤其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即明清时期,文人琴基本不到前台,而退居幕后,在前台活动的基本都是艺人琴家。
由于艺人琴是职业性的,所以它和文人琴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等都有差别。艺人琴家弹琴首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不是自娱的,而是娱人的。这种职业性的特点和娱人性的动因使艺人琴更注重技术的打磨和推敲。因此,艺人琴家技艺大都非常高超,使他们名垂青史的正是他们高超的技艺。在他们看来,“技”是一个核心范畴,琴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艺人琴家要想以自己的艺术表演征服别人、打动别人,就必须在技术上不断提高,必须不断地打磨技巧,从而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样一种技术上的炉火纯青,就成为艺人琴家心目中的演奏之“道”。这个道就是庖丁本身所理解的“道”,即“技中之道”,而非文惠君所讲的“技外之道”。
事实上,每一个艺人琴家都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古琴演奏的技巧,而训练技巧的目的,则是要超越技巧,乃至超越演奏,进入比技巧更高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样?艺人琴家们对它做过许多的描述。宋代海南道人白玉蟾谈到著名琴家吴唐英的琴艺是:“弦指相忘,声徽相化,其若无弦者。”“相忘”、“相化”,就是消解,是指“弦”与“指”、“声”与“徽”之间的界限不再存在,亦即技术被完全把握后而不再存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因为完成了对技术的超越而进入更高的“道”的境界。近代琴家祝风喈曾自述自己的琴艺五年一变,一共三变。他说:“仞变知其妙趣,次变得其妙趣,三变忘其为琴之声。”其“知”、“得”、“忘”,就是三个不同的境界,而惟有“忘”,才能算得上是“道”的境界。“忘”就是超越,对技术与演奏本身的超越。他曾描述过自己所达到的这种超越境界是:“每一鼓至兴致神会,左右两指不自期其轻重疾徐之所以然而然。妙非意逆,元生意外,浑然相忘其为琴声也耶!”这正是技术消解后所出现的一种“物我相忘”的境界。古代琴家常常描述自己超越“技”的阶段后进入这种“物我相忘”亦即“道”的境界,并加以特别的推崇。北宋朱长文在讲到先秦著名琴家师文琴艺时说:“君子之学于琴者,宜正心以审法,审法以察音”,是说初学者要经历的一个长期过程:致力于处理心、法、音等各个环节;等到进入更高的阶段后,“则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此时,一切都融化了,技法、法则、规律都不存在了,它们已经转化为演奏中的一种自发的要求和行为。正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
艺人琴家能够达到并体会出这种境界的很多,北宋僧人琴家则全和尚说:“仆侍先子宦游,因入室烧香,得蜀僧居静字元方直指云:‘每弹琴,是我弹琴、琴弹我。’当下顿悟。”在达到弹琴的极致时,不知是“我弹琴”,还是“琴弹我”。这样一种“道”的境界,和文人琴家所强调的“道”内涵是不一样的,这种“道”是技中之道,是完成了对“技”的解决而进入的自由境界,它不能通过其他东西来追求。离开“技”,“道”就追求不到,只能走“技”这条路才有可能进入
此“道”,但并不是所有走这条路的人都能进入,只有在攻克“技”的堡垒之后,它才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但要真正实现它却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我们在同技术的长期接触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将“技”等同于“艺”,将“艺”等同于“道”的认识障碍,难以从对“技”的解决过程中进入真正“道”的境界。
三、两种技——道关系的相通性
可见,在古琴两大传统中,体现的这两种技道关系截然不同,一为技外之道,一为技中之道。从逻辑学上讲,两者正好相反,互相矛盾,但仔细分析一下,则又有着一种相通性,或者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基础不只在古琴演奏中才有,而是在《庖丁解牛》故事本身就已经蕴含着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庖丁解牛过程中的相通性。
先看“技中之道”,也就是艺人琴的“道”。在庖丁所讲技道关系当中,他所讲的是原始关系,它所具有的涵义是原始涵义。这个涵义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我们对事物要有一个不断深入把握的过程,事物的规律被全部把握之后,我们便进入“道”的境界。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很相吻合。马克思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是事物的规律性,当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必然性后,我们就获得了认识的自由。所以,无论在古琴方面还是在庖丁解牛方面,我们不仅仅要对事物的必然性进行认识,还要顺随事物的必然性进行实践。宰牛和弹琴都是操作即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他是如何步步深入地去把握必然、进入自由境界的呢?
在庖丁解牛的过程中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无非全牛”,即见到的仅仅是一个牛的整体,它的内部肌理尚不清楚,故此时的牛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混沌状态。第二个环节是“未见全牛”,即:经过三年摸索后,已经将牛的内部骨骼肌理摸得一清二楚,这时见到牛,呈现出来的不是牛的整体,而是一个框架结构,一个肌理、纹路、骨骼的立体“模型”。这是对事物的规律在认识层面有了充分的把握,进入对必然认识的自由王国。但这还不是最后亦即最高的境界,因为它还停留在认知阶段,尚未进入实践。马克思说,哲学仅仅解释世界,但关键是要改造世界。所以接着便有第三个环节——“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环节。他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说的便是实践状态。光有认识是不够的,还要把认识到的必然转化到自己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去。这是一个更艰苦但更有意义的过程,是行为对必然的掌握而达到的实践的自由。在表述了这三个环节之后,他还进一步解释其原因,即达到这一境地的原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以无厚入有间”。刀实际上是有厚度的,筋肉关节之间的空隙实际上是极小极小的,但你有了对对象必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之后,它的厚度便大大缩小,空隙也大大扩展,你的自由也就能够得以实现。这说明,只要认识并在实践中体现了这种必然规律,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就能够感到一种彻底的、完全的自由。换一种说法,我们能否获得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在现实空间的大小,而在于对必然的把握和遵循程度如何。中国哲学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非常强调这种道理,体现这种智慧,就象在《庖丁解牛》中所展示的那样。
至于“技外之道”,即文惠君理解的技道关系,只是一种引申义,而不是原始涵义。文惠君讲:“善哉,技盖至此乎”。这里,“此”指的还是技术。接着经过庖丁的一番解释之后,他又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所以,在这个文本中,“养生”是文惠君所领悟的“道”,也是郭庆藩等许多读庄解庄者所理解的“道”。“养生”对于“宰牛”来说,是技外之事,两者非为一体,而是两个并存的事体。用符号学的话说,一是“所指”,一是“能指”。但是,在“养生之道”和“宰牛之技”中又确实存在着一种同构性。这种同构就是一个道理: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宰牛要掌握牛的肌理,把握牛的肢体结构的规律,才能最有效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更好地保存自己(刀)。养生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最有效、最深入地掌握“人的生命的机理”,不仅要认识人的生命的规律,还要在行为上遵循它,才能够达到养生的目的,实现生命的自由。孔子讲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是认识事物的必然,是最低级的阶段;“好之者”是一种心理的向往,是较高一级的阶段;只有“乐之者”,即在实践中因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获得自由、感到快乐者,才算得上是最高级的阶段。而这种自由和快乐,恰好是“技外之道”和“技中之道”所共有的内涵,它们都表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所以,表面上两者截然相反,互相矛盾,实际上则是相通的。
在庖丁解牛的层面它们是相通的,那么,在古琴演奏层面上,即在文人琴和艺人琴的层面上,它们是否也相通呢?
我在将古琴传统分为文人琴和艺人琴两个传统,把它们描述成分分合合的两条线时,有人同我讲,你这样不是把好好的一个古琴整体给分裂了吗?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因而人类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也总是从一分为二开始。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说明我们对这事物还没有形成认识。从古琴演奏层面看,文人琴和艺人琴是否相通,就看他们在弹琴的基本精神上是否相通。我们说过,文人琴的“道”属于“技外之道”,它的内涵是技术以外的东西。那么,文人琴所指的“道”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总体而言,就是指人与天地万物都进入一种和谐状态。汉代桓谭从大处落墨,认为琴能够“合天地之和”。魏时嵇康则从个人心境人手,强调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此后述说琴的修身理性功能的就更多,如白居易的“心积和平气”,“恬淡随人心”;“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苏轼的“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朱熹的“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等。这里所描述的弹琴而臻于“道”的境界,就是通过对自己心灵的调整,而实现“物我合一”、“万物一体”的和谐境界,亦即中国哲学所强调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在现实的物理世界当中,事物都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去批评古代哲学家,认为“物我合一”的精神体验不可能达到。其实,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感觉到我已经不存在了,而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的境界无论在古人还是今人这里都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体验往往不被知觉,或是达到这种体验的人越来越少了。琴之所以能成为琴人修身养性的道器,就是因为琴有这方面的非凡功能。古琴特有的音响效果以及操持方式能帮助人进入这种境界。相比之下,琵琶、二胡、笛子等要稍差一些。在第一种意义层面即“技外之道”上,它进入了一种“物我合一”的自由状态;第二种意义上的“道”亦即“技中之道”则表现了人与琴、音与意也融合为一。弹琴时,
当人与琴、指与弦、音与意达到高度统一时,也就与整个世界融合不分了。我们经常说“陶醉”于音乐之中,“陶醉”就是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艺人琴通过对“技”的超越,使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而进入“道”的化境。这种化境便是“物我交融”的境界,这恰好与文人琴所追求的“道”的境界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文人琴还是艺人琴,它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修持途径来达到目的,也无论琴弹得好坏,都能达到“物我统一”的最高境界,这也是琴为什么能长久地在民间流行的原因。所以,在深层次上,文人琴与艺人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四、对今人的启示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个话题对今人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从事音乐和从事音乐演奏的人来说,我认为意义很大。由于这方面的东西现代演奏理论很少讲到,现代演奏理论更多地进入到一个操作层面中去了。呈现出的理论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更能显出传统古琴演奏理论中这些思考的可贵。
我们先来看艺人琴的技道关系给人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弹琴需要技巧,而且必须完成对技巧的超越,但这个超越只能通过技巧本身来实现,最后达到一种状态,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得意忘言”的状态。对技术的掌握,都要经过一个“得意忘言”的环节才能进入更高的“道”的境界。言是用来表达意的,掌握意后,言就可以丢掉,而且,在庄子看来,是必须丢掉。如果不丢掉,“道”的境界就永远不会出现,你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这个点上而得不到提升。为什么“得意”后要“忘言”?我喜欢打这样一个比方,比如:人要过河,必须有船,船到对岸,想上岸就必须离开船。如果始终没有离开船,那就意味着你还没有到达彼岸,虽然此时只有一步之遥。同样,言和意的关系也如此,通过言把握意,意把握后就须丢掉言;如果还是死死把握(拘泥于)言,说明你还是只注意到形迹,还没有真正把握“意”。真正把握“意”后,“言”就变得不再重要,正如人上岸后,船对你来说就显得没有意义一样。如果还是抓着不放,只会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其实,学习任何东西都包含着这个道理,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在你真正掌握它以后,你就会自然忘掉它的形迹。
再看演奏。要达到这样一种演奏,必须完成三个超越。首先,是对技术的超越。要想进入演奏之“道”,必须完成对技术的超越。技术具有二重性,好像一把双刃剑。从技术作用的对象看,它既是对对象的敞开,又是对对象的遮蔽。它的意思是,通过技术打开世界,使世界归于我,所以技术是伟大的;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遮蔽,用来做家具的木头不能再用来做船,木头当中能够做船的潜在性能没有了。所以说,技术在创造一个方面时,也消灭了另一个方面。再从技术使用主体来看,它既是对人的能力的扩展,又是对人能力的“掏空”。有了技术,人的能力得到延伸,电话是对人的听觉的延伸,车船飞机是对人的行走能力的延伸,显微镜和望远镜是对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计算机是对人的大脑思维能力的延伸……可以说。各种技术发明都延伸了我们的感官,扩大了我们的感觉范围,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同时又是对人内在能力的“掏空”,在车、船发明之前,人靠两条腿走路,肌肉很发达;车、船发明后,人们用它代替了双腿,使我们步行的能力大大降低;同样,有了计算器后,我们的口算和心算能力也明显退化。这里我并不是要反对技术,取消技术,而是要看到它的二重性,警惕技术对我们的伤害。这种把艺术仅仅看成是技术的现象,在各种艺术中普遍存在,并且古今皆同。即以古代为例,古代诗歌当中,就存在着一种把诗看成技术即平仄安排的倾向,并且越来越严重,最后使诗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诗歌形态——词。词开始非常自由,但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也慢慢地变得技术化,终至僵化。结果,词也衰落了,然后又有了曲。可见,形式和技术是有着“自发展”的本能的。诗的本意并不是平仄的安排,而是对人生感受的抒写;同样,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表达人生感受的特殊方式。但随着艺术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它的技术化也就越来越严重,反而是业余人员的作品更与艺术的本性相通。所以,如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你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永远只能停留在匠人的水平。
除了技术的超越外,还有两种超越,一是对谱本的超越,即不要被谱本局限。谱本是乐曲的一种定格了的存在,而音乐本身是“活”的。要使谱子“活”起来,就必须超越这个谱本。另一超越是对演奏的超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地是在演奏,但却又要超越演奏,进入一种非演奏的演奏状态。我们在意识到演奏时,就会意识到谱本、技术、听众,从而受到这些因素的束缚。只有把演奏看成生命自然而然的行为,才能在音乐追求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嵇康有一首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样的演奏才是使人快乐的,才是我们向往的、真正使人自由的活动。但是,对演奏的超越并不就是一种熟练。“熟”只是在技术上有所进展,它本身尚未进入道的境界。当“熟”而又未能进入更高境界时,它便会转化为“油”,即油滑,漂浮。这样的音乐没有力量,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明代琴家张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练熟还生”。这里的“生”不是指“生涩”,而是指音乐演奏中的“生气”,一种生命状态、生命张力和生命感觉。在演奏过程中,意识不到自己在演奏,才是真正的演奏,才是与生命感觉融合在一起的演奏。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之所以拒绝舞台演出,除了他个人的其它原因外,我想,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于他来说,一旦走向舞台,面对着听众,就会唤起他的演奏意识,使他难以完成对演奏的超越。我说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大家向古尔德学习,也拒绝舞台演出,而是提醒大家在舞台演出时,一定要超越演奏状态,并且是在面对听众的舞台演出时超越演奏状态。古人有诗云:“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只要是真正的隐士,不见得非要住到深山老林之中;同样,真正有道的演奏家,不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客厅里抑或录音棚中,都一样能够达到非演奏的演奏状态。艺人琴告诉我们必须完成超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技的超越和对演奏的超越。
文人琴中的技道关系对我们今天的演奏也是有着重要启示的。表面上看,文人琴中的“道”是另外一种东西,似乎与音乐无关,如:道德修养、人文修养,但在更深层面上,它对音乐演奏有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没有这个支撑,音乐就是一杯白开水,索然寡昧。陆游在讲到学诗时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只有认真体验人生,并且对生命有了真切感悟时,写出的诗才可能有血有肉,才会有生命的张力,才能够对别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仅仅靠诗的形式、格律写出的诗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们正处在过分技术化和形式化的时代,以为艺术创造的奥秘就在于用学来的形式技法去编织一首一首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很难让人感动的。李叔同的《送别》,简简单单几句词却感动了几代人,词很简单,但表达出来的却是李叔同和无数文人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审美意象和人性中最深沉的依恋,一种使你挥之不去的令人心动的元素。现在的艺术作品很少有这种感动力,原因就在艺术的技术化,艺术失去对“道”的追求。因此,经常回到传统艺术理论之中,感受他们对艺术之道的深沉思考,可以弥补我们现代艺术的一些缺陷和不足,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社会的游戏规则是这样,不可能凭个人的力量来改变它,但每个人都来守持这个艺术之“道”,领悟艺术中“技”与“道”的深刻联系,我想,还是能够焕发出艺术的活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