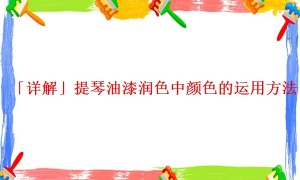在巴勃罗·法里亚斯(Pablo Farias)的工作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的味道。巴勃罗坐在工作台前,正在给最新的小提琴上漆。刷子轻抚着琴上光滑的枫木,来回缓缓滑动。在俯瞰克雷莫纳历史中心的窗户旁,两把蓝色的小扶手椅仍然包裹在透明塑料里。“我刚搬到这个工作室,”他说着,眼睛没有离开小提琴。“我本来准备3月份开这家店的,但后来病毒大爆发,政府的封锁令迫使我取消了计划。”巴勃罗戴着口罩的脸庞似乎在苦笑。
克雷莫纳(Cremona)是一个拥有7.3万居民的城市,位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Lombardy)的南部边界。2020年2月,伦巴第成为了病毒爆发的中心,也是欧洲首次爆发疫情的地点。根据官方数据,新冠肺炎已在克雷莫纳省(克雷莫纳市及周边城镇)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和6600例确诊病例,目前正对其经济造成压力。尤其是,疫情爆发正威胁着小提琴制作技艺,而这一技艺一直是克雷莫纳工业的历史引擎,并使其botteghe(意大利语中“作坊”的意思)闻名于世,令克雷莫纳成为疫情危害全球文化和艺术的微观反映。
阿根廷出生的工匠巴勃罗·法里亚斯(Pablo Farias)正在给小提琴上漆,他是目前在克雷莫纳生活和工作的160多名制琴师之一。
自16世纪起,克雷莫纳就开始有了手工制作的弓弦乐器。克雷莫纳也是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pari)的家乡,他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制造者。斯特拉迪瓦里过去制作乐器的车间在1934年被拆除,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谈论他。学校、住宿加早餐旅馆(bed and breakfasts,又称民宿)、体育中心、餐馆和咖啡馆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估计,他一生共制造了960把小提琴。可如今,他的事迹正在苟廷殘喘。
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文化遗产名录里,这个城市的工匠以制作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独特手艺而享有国际声誉。他们组装超过70块木头的模具,不使用任何工业材料。长期以来,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传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小提琴制造者——也被称为制琴师(luthiers)——来到这里从事贸易行业。
行业的中心
出生在阿根廷的帕布罗·法里亚斯(Pablo Farias)是160多名制琴师中的一员,他们大多毕业于克雷莫纳的国际小提琴制作学校,目前在这座城市的鹅卵石小巷生活、工作。在车间的阴凉处,他们将枫木和云杉木加工成价值数千欧元的乐器。“价格因制琴师和市场而有所不同,”斯特凡诺·佩斯基奇(Stefano Trabucchi)说,他在1992年开了自己的作坊。他指着挂在贯穿车间的钢缆上一排小提琴解释说:“平均价格约1万欧元(1.17万美元;9150英镑),但有些小提琴的价格高达2万欧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意大利每年出口的弓弦乐器价值660万美元(540万英镑),主要销往日本(268万美元)、美国(87.3万美元)、香港(79.4万美元)和中国大陆(35.3万美元)。仅克雷莫纳一家就贡献了其中的80%,即每年超过530万美元。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造商依赖于两类客户的订单:个人和经销商,他们通常在商店里以两倍的价格将小提琴转售给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和音乐家。在克雷莫纳制作的小提琴可以是“Straparius”,灵感来自于制琴师斯特拉迪瓦里(Strapari)的设计,也可以是“Guarneri del Gesu”,基于18世纪制琴师的模型——也是斯特拉迪瓦里的竞争对手瓜尔内里(Giuseppe Guarneri)。斯特凡诺说:“对未经训练的人来说,这两个型号看起来很相似,但他们的形状略有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制作乐器的过程至少需要六周时间。因此,大多数工匠通常一年制作不超过十把小提琴。”
在乔吉奥·格里斯莱斯(Giorgio Grisales)商店的一位年轻制琴师。格里斯莱斯是该市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pari)小提琴制造商联盟的领头人。
50岁的制琴师帕特里克•奥里皮(Patrick Orippi)曾是一名木工和雕刻工,他在老城大门上的小作坊里独自工作。一束光线透过窗户反射在工作台上。“通常情况下,我一年要制作六、七件乐器。我在1月份把最后一把小提琴运了出去,所以从封城以来,生意一直很不景气。”封城迫使一些非必要商店关闭,许多经销商冻结甚至取消了订单。“冠状病毒让我暂停了订单,”奥里皮说。如果一个订单没有完成,制琴师不会为他所做的小提琴支付报酬。和奥里皮一样,法瑞斯也没有雇员。他说:“我通常在乐器上工作两到三个月。(取消订单)基本上意味着工作两三个月没有报酬。在封城期间,制琴师甚至不允许返回他们的商店,也不允许他们在紧闭的百叶窗后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规则就是规则,我明白,但这个规则不太合理。”法里亚斯说。
封城后的生活
6月底,在奥里皮的工作室外,街道上静悄悄的。该地区的封锁已经放松了近两个月,但仍然没有游客在老城区狭窄的小巷里闲逛。孩子的脚步声在石墙中回响。法里亚斯说:“在封锁期间,气氛几乎是无法忍受的。我能听到的只有救护车的警报声,一遍又一遍。那些在阿根廷的兄弟和朋友在电话里安慰我,但他们也不容易。他们担心我。”由于被迫和女友呆在家里,法里亚斯不再做小提琴,开始做面包。他笑了一会儿说:“就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
这对克雷莫纳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佩斯基奇说:“我有一些朋友和同事感染了病毒,幸运的是最终康复了。”封城前,他和家人离开了克雷莫纳,之后他一直呆在山上的房子里。“当我回来时,空气中充满了悲伤,城市是空的。即使是现在,这个城市也在挣扎着重新站起来。这里的小提琴制作者也是如此。”
克雷莫纳的制琴师们正在努力重新在这个冠状病毒爆发前就已经面临压力的行业中站稳脚跟。“在这座城市做制琴师是一种独特的经历,”特拉布基说。你有机会与优秀的同事交流想法,竞争迫使你日复一日地提高,但市场现在已经饱和。1990年代初,当佩斯基奇第一次涉足时,这座城市大约有60名小提琴制造商。现在,数字几乎翻了两番。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制琴师、该市“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pari)小提琴制造商联盟的主席乔治·格里斯(Giorgio Grisales)说:“一把小提琴可以使用200多年,有时甚至更久,因此市场很快就会饱和。”
帕特里克·奥里皮(Patrick Orippi)在制作一把小提琴,他通常一年制作六、七件乐器。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拿起一把等待运往马来西亚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细长的手爱抚地摸着这把乐器的背部,这是他唯一的雇员马里奥制作的。“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进入的市场,过去还好。现在,冠状病毒引发的危机将改变我们熟悉的行业。”
对古典音乐的打击
古典音乐行业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全球范围内的交响乐团都陷入了财务困境。他们被迫取消音乐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收入骤降,还会解雇音乐家。“音乐家是我们的终极用户,而目前他们处于水深之中,”莫拉西(Simeone Morassi)说,他是该市一间最古老的作坊老板,也是意大利制琴师协会的副主席。“过去几年里,我把自己的四件乐器卖给了NHK交响乐团(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通称“N响”)的音乐家。那是日本一个主要的交响乐团。它如今正在苦苦挣扎,损失了数百万日元。”
另一家日本乐团——总部位于东京的东京交响乐团(TSO)——由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演出取消,在2月底到4月初期间损失了约5000万日元(47.1万美元)。而在克雷莫纳小提琴制造商的另一个重要市场美国,“最近几周,许多乐器店被迫关闭,”佩斯基奇补充道。音乐家和经销商的财务紧张导致了乐器行业的停滞,影响小提琴制造商和市场上的其他主要参与者。莫拉西说:“弦乐器的制作者也有麻烦了。音乐家通常在30到90天后更换琴弦,但现在一切都被搁置了,制作这些琴弦的奥地利和德国人都很痛苦。这种情况极其微妙。”
2020年上半年在法兰克福和北京的两场最重要的国际交易会被取消,这进一步影响了制琴师。在这些展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提琴制造商通常会竞相开拓自己的市场,加强与经销商的关系,并试图创建新的经销商。“取消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格里斯说。“今年10月,上海还将举办另一场重要的博览会,那时就会明确。”然而,格里斯担心,来自意大利的人可能会比来自感染率较低国家的人受到更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造商将无法像竞争对手那样参加博览会。”
佩斯基奇说,”新冠病毒将成为这座城市小提琴制造者的分水岭。”
根据格里斯的说法,这场危机对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他表示:“在这个由160名制琴师组成的联盟中,约有60名在苦苦挣扎。”一些国家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难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我认识一些制琴师,他们从去年11月开始就不卖乐器了,”格里斯说。“我们谈论的是那些有孩子、要付房租、入不敷出的人。该联盟的两名手艺人还没有收到政府向自由职业者承诺的600欧元(699美元),他们需要这笔钱。”
格里斯朝他左边的店铺后面望去,他的三个年轻工匠正在那里对珍贵木头塑形、雕刻和上光。“我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总的来说,我在维持生计,其他同事也一样。但试想一下,在一个较小的作坊里,只有一名工匠,他被迫停工三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小提琴的需求下降——由于目前的危机,这是必然的——克雷莫纳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每个人。“冠状病毒将是我们的分水岭,”佩斯基奇说。他的工匠马里奥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对大师的话无动于衷。佩斯基奇说,“这个市场似乎有无限的潜力,但它将不再扩张。在这个城市,数十家工厂可能都得关闭。”
与此同时,那些想要开办工作室的人将被迫等待,至少现在是这样。特拉布基说:“开始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在他身后,马里奥正在调整小提琴的琴弦。他凝视着大师,好像在征求让他说话的默许。“我37岁了,在这里工作了16年,一直很享受这种归属感,”马里奥说着,放下了乐器。“当然,我梦想自己创业。但你必须面对现实。目前开一个车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将来的风险也会非常高。”马里奥回头看了看小提琴,轻轻地转动着手中的乐器。总有一天会有人拉奏它,但不是今天。今天,克雷莫纳的小巷里没有音乐。